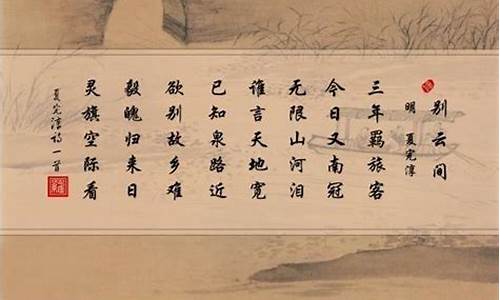挤满了怎么写-挤得满满当当
1.韩红创作《天亮了》的背景是什么?
2.满满登登的意思
3.拥挤的车厢让我难忘的作文
4.用满满当当造句
5.满满当当拼音
6.散文 | 鲍尔吉·原野:不知不觉,风吹薄了人
韩红创作《天亮了》的背景是什么?

《天亮了》这首歌与她的养子潘子灏的身世有关。
1999年10月3日,在贵州马岭河风景区,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,在缆车坠落的那一刹那间,车厢内来自南宁市的潘天麒、贺艳文夫妇,不约而同地使劲将年仅两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。结果,孩子只是嘴唇受了点轻伤,而只有2岁半的潘子灏变成了孤儿。
这个生命的故事,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,她以这个令人震撼的事件并以小孩的口吻,创作了《天亮了》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,并经过多方联系,领养了这个大难不的小孩。
一曲《天亮了》开启公益之路
从那时开始,韩红走上了漫漫的公益之路。
2003年4月,韩红到美国参加世界妇女领导峰会,留给她的发言时间只有1分50秒,她只好简单介绍了家乡西藏的教育情况和藏族文化的发展,然后即兴唱了一首山歌。或许被她的歌声打动,散会后,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领导纷纷拨款给西藏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会。
韩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——为失聪儿童募款;赴港参加海啸赈灾义演,并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10万元;参加“为残奥会助威”活动;向贫困地区捐赠100口“母亲水窖”;2008年,她将个人演唱会的30万元收入捐给3所少数民族孤儿学校。
2008年5月12日,汶川地震发生,韩红焦急万分,先是在北京为灾区募捐100多万元。后来在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,以最快速度启动了“韩红爱心救援行动”,5月21日,韩红和救援志愿队从北京启程,奔赴灾区一线。
2012年7月6日,“韩红爱心百人援蒙”在北京出征。7月的内蒙古高原烈日炎炎,许多患者千里迢迢赶到现场,小小的义诊帐篷总是被挤得满满当当,27位国内知名医疗专家顶着酷暑为草原牧民义诊。
满满登登的意思
满满登登的意思是极丰富的,富裕的,装得很多的。
成语出处:
1、《吉林日报》1981.1.23:“大包小包的,把一辆送站的毛驴车装得满满登登的,乐颠颠地登上了进关的车。”
2、古华《芙蓉镇》第三章:“学校、礼堂、招待所都住得满满登登的。”
成语用法:作定语、状语;形容很丰富。
感情褒贬:中性成语。
满满登登的反义词:空空如也;满满登登的近义词:满满当当。
“满满登登”造句:
小药筐已经被装的满满登登的,再也装不下任何一株草药了。
每一船每一箱,都塞的满满登登的,站在周围的人,都有一种被钱财光辉所笼罩的神奇感觉。
云飞扬看着满满登登的广场现在已经不再拥挤了。
饭堂院当中那五张桌子挤得满满登登。
紧接着,他双手上下齐飞,仅仅片刻,肉食已是满满登登装了一篮子。
拥挤的车厢让我难忘的作文
人生中的每一份感动,都让人难以忘怀;在人生的岁月中,每一次感动,都让人不得不泪水涟涟。有时,那份感动又来得那么突然。
在补习班上完课的时候,天上还是一直下着鹅毛大雪,我一直站在那儿等公交车。一会一辆车过去了,一会又一辆车过去了……虽然车很大,但车上都做满了人。这时,又一辆车来了,车上没有满满当当,比刚才过去的那一辆好多了,至少还可以上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,在这个飘雪的日子完全可以。
上了车,把老早就准备好的一元钱放进去了,非常高兴,至少不要再忍受那刺骨的寒风和冰凉的雪。又上来十几个胖胖的人,车厢里顿时满满当当的,如同百万大军,还好我刚才早上了一站,要不然又要再等了。
这时,车再次开了,车上矮小瘦弱的我被这些庞然大物挤得就像面包一样,慢慢的变小,甚至喘不过起来。突然,一个陌生的叔叔站了起来,一把抓住我,指了指刚才他坐的座位,笑着说:“小朋友,你坐这儿!”
说完,那位叔叔站进拥挤的人群中,我坐在了他刚才的座位上。再看这位叔叔,被拥挤的人群挤得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往后。此时此刻,我被这位叔叔感动了,他把这么好的一个座位让给我,自己站在人群中,会不会被挤得晕头转向。
我真没有想到,在这样恶劣的'天气下,天下还有对我这么好的人啊!我真想对他说:“谢谢你,叔叔!”但是,他很快被上上下下的人流,拥挤得不见踪迹。
认真对待生命中认识不认识的人,仔细感受生命中认识不认识的人,你会发现在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,都充满了感动,都是对你的爱。
用满满当当造句
满满当当造句如下:
1、满员的车厢,满满当当的喧嚣与琐碎。
2、祝你幸福满满当当,快乐洋洋洒洒。
3、衣柜里满满当当都是质量低劣。
4、心是这样满满当当的压抑感。
5、生活种开始满满当当都是节日的踪影。
6、我的早已空,没有任何人,装满自己满满当当。
7、祝你工作满堂,财运满堂红,福气满满当当,生洋美满满,一切满满意意。
8、一回家就看见满满当当的冰箱和食物柜。
9、把心里的空间留出来,不要让怨气塞得满满当当。
10、法新社报道,特朗普17日的面试安排满满当当。
11、这样一个简单的菜园能使你的沙拉盘6个星期都满满当当的。
12、祝你生活圆满,爱情美满,快乐填满,美酒斟满,祝你一生一世,福气满满当当。
13、回想起来,哪怕只有一个眼神也觉得整个人都满满当当的。
14、此时教室里已经满满当当的只剩下一个空座位,那个空座位的主人,理所当然就是我。
15、社区活动室里的大圆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菜肴,几十个盘盘盏盏挤得满满当当。
满满当当拼音
mǎn? mǎn dāng dāng。
成语意思
解释:形容很满的样子
出处:清·西周生《醒世姻缘传》第23回:“原来银包不大,止那七两多银子已是包得满满当当的了,那里又包得这十两银子去?”
语法:满满当当作定语、状语;指很满。
示例:阿来《尘埃落定》第一章:“我那小胃很快就给装得满满当当了。”
近义词:满坑满谷
反义词:空空如也
成语造句
(1) 夏日艳阳,快乐照射,祝福满满当当;下雨滋润,快乐滴滴,祝福满心满意。送你快乐,愿你心情满心欢喜;送你微笑,愿你成功满载而归!小满快乐!
(2) 像是倒一根长套索似的,水从满满当当的科克湖里溢了出来,将发绿的金色沙滩淹没,越涨越高,滔滔滚滚流去。
(3) 然而,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将一天的时间填得满满当当,路上的时间一点不留。
(4) 各种车辆把停车场塞得满满当当。
(5) 打开一看,哪里是什么海产品,竟是满满当当的瓜子金。
(6) 本来还算宽敞的三室一厅满满当当挤的全是鬼影不说,就连韦陀像都大了一截,乍一看上去还以为真是个人盘腿坐在众鬼中间一样。
(7) 一想到这里,恐惧顿时充斥了赵林的心中,满满当当的,不过也许是物极而反,恐惧到了极点之后,赵林的身体反而不颤抖了
(8) 在其店门口,捕鸟支网的杆子、铁夹,诱鸟的谷物堆得满满当当。
(9) 秋是高贵的,所有人为她的到来变得格外繁忙。割下一片片稻谷,摘下一架架丝瓜,将红透的苹果采下,把雪白的棉花收集。人们为了迎接她而把一切收拾得整整齐齐,粮仓也因此变得满满当当。
散文 | 鲍尔吉·原野:不知不觉,风吹薄了人
不知不觉,风吹薄了人
文丨鲍尔吉·原野
风里有什么
世上有好多事情弄不清,最弄不清者一为风,二为云。人遇到风。呼来了,呼走了。啥来了,啥走了?不知道。感受过,但一辈子没见过此物。“风”这个词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对风,我们是盲人。就像我们在爱情里是盲人。男人只见过女人,谁见过爱情?
树林里,栎树的小圆叶子微微摇动,是风来了吗?人还没感受到风,树叶却已经招手了。走上山岗,传来巨大的风声,树叶像潮水一样喧哗。一棵树身上不知有多少叶子,而每一张叶子都在动并发出声音。
风穿越绿叶的隧道。而人却没觉得有什么风。细听,听不出清林中的风声从何而来。树叶和树枝只是在抖晃俯仰,竟发出深沉的低音。在主旋律“呜——”结束之后,才是树叶子“刷拉拉”的后伴音。说!“呜——”是谁的声音?
盲人如果来到呼伦贝尔游历,他大脑收获的图景跟明眼人会完全不同,大不同。他看不到雨后的草原在深蓝城堡般的云层下透出的新绿,看不到像刷了石灰粉一样的白桦树互相斜倚,宛如等人来合影,看不到莫尔格勒河如盘肠一般,一里地弯十个弯。陡立的河床上长满了青草。
盲旅人看不到这些,他被呼伦贝尔的风抱在怀里,风拉住他的手旅行。风是另一位盲人,它用一种叫作“风”的手势识别盲旅人的脸,摸他的眼睛、鼻子、脖子和头发。草原的风打扫他浑身上下,衣裤簇簇作响。盲人听到,季风弹拨落叶松的松针,声音似蜂蜜的丝。风捧不起河流的水,却把水的腥气塞进人的鼻子里。
风里有什么?大兴安岭南麓和北麓的气味不一样,盲人的脑部地图定位着白桦林的清甜气味,奔跑结束的马群的骚汗味,被露水打倒的青草的气味,还有风。
风并没有风味,风里只有远方的味。风里混合着高山岩石的苔藓味,低洼地带的泉水、动物粪便和草原上不同的野花的气味。风大度地、悠然地把各处的气味带到各处,又把各处的气味带到其它各处。对野生动物来说,这些气味是博物馆,气味里有所有动物的表情,花和河流的意思。风里的气味是野生动物的生存依据。
小鸟身上有什么味吗?不知道,它们笔直地飞进蒙古栎树林,不知道给树林带去了什么气味。去呼伦贝尔 旅游 的人可能忘记了,小鸟始终在他们头顶飞翔鸣唱。
我提醒自己,每到一个新地方,先听听有没有鸟鸣。事实上,每一个地方都有小鸟的歌唱,除非下雨或刮大风。我听到这些歌唱,满自负,以为别人没听到。他们盯着草原上的野花,笨拙地迈进,忘了鸟鸣。
我闭眼倾听鸟的歌唱,它们的歌声光溜溜的,音节或长或短,歌词不相同。别人告诉我,大部分是云雀和百灵的歌声。然而看不到这些鸟儿,草原上没有树,它们在我头顶什么地方唱呢?只好说,呼伦贝尔有数不清的鸟,边唱边飞,我听到了它们路过时的那一段音频。
又起风了
在树林里走,忽而起风了。这风不算弱,却明净无尘。仰面看绿意连绵的树冠,听到咯嚓的折枝声。一会儿,地上散布断枝。
被风摧折的悉是枯枝,黄褐色,像蛇一样。但杈桠伸张,仿佛不甘心于坠弃。周围的大树那么茁壮,叶子在枝上一片片相互摩拳,在风里把低缓的呼吸声传得很远。
我感到一点悲凉,白杨树粗壮向上的躯干泛着生命的青色,枯枝卧在它的脚下,枯枝已经不能叫作树了。
风止息,在宁静中,我又想到枯枝,也许勿庸替它悲悼。它或许正在感谢于风,将其从弥留中解脱,送还地上,得到盼了许久的安然。它刚刚开始枯干那会儿,树干的汁液已经渐少,枯枝瞅着叶子片片发黄,不知何时飞旋而走。它也许就盼望回到俯瞰了许久的土地上。
但枯枝必须经历萧索的整个过程,不能加快,亦不能减慢。那么,就在风不期然而来之际,这个时刻就叫作大限,也许还是一个庆典。枯枝在离开树的刹那,总要断然一响,清脆之声远远近近都听得见。这声音的脆亮,是痛苦的最后一吼,还是欢愉的意外之音,我不清楚。或许这两种情态都包含其中了。
我不清楚的事情,就不再思索了。人的毛病之一,在于喜欢设出两种结论,然后选择其一。这就导致更深的迷惑。
就在我快要走出这片树林的时候,身后又传来四面八方的簌簌之音。我回头看起伏如浪的树冠,又起风了。
在这样的风里
如果世上有一双抚爱的巨手,那必是草原上透明的风。
风是草原自由的子孙,它追随着马群、草场、炊烟和歌唱的女人。在塞上,风的强劲会让初来的人惊讶。倘若你坐在车里,透过玻璃窗,会看到低伏的绿草像千万条闪光的蛇在爬行,仿佛拥向一处渴饮的岸。
这是风,然而蓝天明净无尘,阳光仍然直射下来,所有的云都在天边午睡。这是一场感受不到的哗变。在风中,草叶笔直地向前冲去,你感到它们会像暴躁的油画家的笔触,一笔一笔,毫不犹疑,绿的边缘带着刺眼的白光。
风就是这样抚爱着草叶。蒙古人的一切都在这些柔软的草叶的推举下变成久远的生活。没有草,就没有蒙古包、勒勒车和木碗里的里面的粮食。因此“嘎达梅林”所回环祷唱的歌词,其实只有一句话:土地。每天,土地被风无数次地丈量过,然后传到牧马人的耳边。
到了夏季,在流水一般的风里,才会看到马的俊美。马群像飞矢一样从眼前穿过时,尾鬃飘散如帜,好像系在马身的白绸黑绸。而这样的风中,竟看不到花朵摇摆,也许它们太矮了,只是微微颤着,使劲张开五片或六片的花瓣。
在风里,姑娘的蒙古袍飘飘翻飞,仿佛有一只手拽她去山那边的草场。这时,会看出蒙古袍的美丽,由于风,它在苍茫的草地上抖搂亮丽。而姑娘的腰身也像在水里一般鲜明。
背手的老汉前倾着身子勉力行进,这是草原上最熟悉的身影。外人不明白在清和天气,他走得何以如风中跋涉。风,透明的风吹在老汉脸上,似乎要把皱纹散开,把灰色的八撇胡子吹成小鸟的翅膀。
在这样的风里,河流仍然徐徐而流,只是水面碎了,反映不出对岸的柳树。百灵鸟像子弹一样“嗖”地射向天空,然后直上直下与风嬉戏,接着落在草丛里歌唱。它们从来都是逆风而翔,歌声传得很远。
风吹草动
五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,我骑车去辽宁大学操场跑步,没按惯常路线走,转道从礼堂那边绕行。接近篮球场时,看到方形草坪上,草叶闪闪发光,马兰在树墙外悄悄开放蓝花。老校工在剪树。
草坪的草是咱们说的进口品种,娇嫩翠绿如染织的地毯。而比地毯更高明处在于草们在风的驱赶下作出的精致舞蹈。洋草修长柔韧,色泽是画家笔下才有的晶莹的浅绿,而草叶背面在绿中衬一抹银灰。
透明的风在这里和草开展欢愉的 游戏 。有时草叶急急如“之”字蛇行;有时像波纹一圈圈荡开,仿佛投入了石子,或者如 体育 场上的观众臂膀相牵此起而彼伏的场面。面对这些美丽不知疲倦的草叶,你尽可以想像它们在骑马、哗变、演习八卦掌(团体项目)与诺曼低登陆。
谁知“风吹草动”四字在此竟有如此生动的演示。这与我在草原和乡村看到的草景都不同。后者是民众,这边是草舞蹈团。我甚至想冒着挨骂的危险说:“还是外国的草好啊!”或“还是外国劳动人民的草好!”
此时是下午,天边摆满五月的白云。雨才歇,蝴蝶和蜜蜂都没有出来,楼角上的广播喇叭里传出学生播发的知识稿件——海洋资源远远多于陆地资源。
与“草舞蹈团”隔一道树墙的是一排马兰,开着淡蓝的花。它们像一群蹑足而走的乡村姑娘,十七八岁,想引人注意又怕异样的目光。
我忽地想起萧娴笔下的兰花,也是这样轻盈淡雅。此画是一本杂志的封底,20年前糊在我家裂缝的门板上挡风。我为想起这幅画以及萧娴的名字而惊讶。
在都市里,一个人被裹胁于车马人流之间,偶尔脱身却见马兰花静姝一隅,你甚至不好意思自己的东奔西走。我蹲下,专注于花草。老校工环臂持大铁剪“嗒嗒”开合,然后俯察,如理发师侧首找寻那人头上杂毛。我恍然,马兰花、老校工弯腰的姿态和草的舞蹈,是一幅让人屏息而视的画面。
在平静的生活中,天地间会突然出现美不可言的胜境。我庆幸看到了它。
这时,老校工回头看我,汗里的盐使他眼角眯着,表情似有不悦。一人站在另一劳动者身后无理由地观望,当然令人不悦。其实我想多看一会儿。老校工二度一瞥,我走了,美丽的草和马兰都是他的。
日常景色在朴素的外表下会突然爆裂内里的美,明灿高扬。与之遭逢已经很难,而遭逢之后无法勾留是另一无奈。人们跋山涉水去拜谒天下名景,譬如泰山峨嵋时,究竟有多少人看到了它真正摄人魂魄的美?美像闪电一样,不可能总是出现。
它的出现,必有晨夕,明暗乃至风与雨的交关组合,像盛妆的大师出现在舞台上。而多数人在泰山峨嵋所遇,仅是一场没有演出的空寂剧场而已。
有人说,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,只在某年某月的几天,至多一个星期便寂落了。人们娶来的妻子,多数已经不包含这几天了。如同花朵在空谷里的绽放,它的美属于神,而非男人或女人。
这么小的小风
最小的小风俯在水面,柳树的倒影被蒙上了马赛克,像电视上的匿名人士。亭子、桑树和小叶柞的倒影都有横纹,不让你看清楚。而远看湖面如镜,移着白云。
天下竟有这么小的风,脸上无风感(脸皮薄厚因人而异),柳枝也不摆。看百年柳树的深沟粗壑,想不出还能发出柔嫩的新枝。人老了,身上哪样东西是新的?手足面庞、毛发爪牙,都旧了。
在湖面的马赛克边上,一团团鲜红深浅游动,红鲤鱼。一帮孩子把馒头搓成球儿,放鱼钩上钓鱼。一条鱼张嘴含馒头,吐出,再含,不肯咬钩。孩子们笑,跺脚,恨不能自己上去咬钩。
此地亭多,或许某一届的领导读过醉翁亭记,染了亭子癖。这里的山、湖心岛、大门口,稍多的土积之成丘之地,必有一亭。木制的、水泥的、铁管焊的亭翘起四个角,像裙子被人同时撩起来。
一个小亭子四角飞檐之上,又有三层四角,亭子尖是东正教式的洋葱头,设计人爱亭之深,不可自拔。最不凡的亭,是在日本炮楼顶上修的,飞檐招展,红绿相间,像老汉脖上骑一个扭秧歌的村姑。
干枯的落叶被雨浇得卷曲了,如一层褐色的波浪。一种不知名的草,触须缠在树枝上。春天,这株草张开枣大的荚,草籽带着一个个降落伞被风吹走。
伞的须发洁白晶莹,如蚕丝,比蒲公英更漂亮。植物们,各有各的巧劲儿。深沟的水假装冻着,已经酥了,看得清水底的草。我想找石头砸冰,听一下“噗”或“扑通”,竟找不到。
出林子见一红砖甬道,两米宽。道旁栽的雪松长得太快,把道封住了,过不去人。不知是松还是铺甬道的人,总之有一方幽默。打这儿往外走,有一条小柏油路,牌子上书:干道。更宽的大道没牌子。
看惯了亭子,恍然想起这里有十几座仿古建筑,青砖飞檐,使后来的修亭人不得不修亭,檐到处飞。
我想在树林里找到一棵对早春无动于衷的树,那是杨树。杨树没有春天的表情,白而青的外皮皲裂黑斑,它不飘舞枝条,也不准备开花。野花开了,蝴蝶慢吞吞地飞,才是春天,杨树觉得春天还没到。杨树腰杆太直,假如低头看一下,也能发现青草。青草于地,如我头上的白发,忽东忽西,还没连成片。杨树把枝杈举向天空,仿佛去年霜降的那天被冻住了,至今没缓过来。
鸟儿在鹰不落的上空飞,众多的树,俯瞰俱是它的领地。落在哪一棵上好呢?梨树疏朗透光,仪态也优雅,但隐蔽性差;柏树里面太挤了,虽然适合调情;小叶柞树的叶子还不叶,桑树也未桑。小鸟飞着,见西天金红,急忙找一棵树歇息。天暗了,没看清这是一棵什么树。
风到底要吹走什么
湖水的波纹一如湖的笑容,芭蕉叶子转身洒落了一夜的露水。晃动的野菊花仿佛想起难以置信的梦境;旗帜用最大的力气抱住旗杆,好像要把旗杆从土地里拔出——它们遇到了风。
风同时用最大和最小的力量吹拂万物。它吹花朵的气流与人吹笛子的气流仿佛,风竟有如此温柔的心,这样的心让湖水笑出皱纹。水原本没有皮,风从湖的脸上揪出一层皮,让它笑。
风到底想干什么呢?风让森林的树梢涌动波涛,让树枝和树叶彼此抚摸,树枝抽打树枝,树叶在风里不知身在何处。风在树梢听到自己的声音变为合唱,哗——,哦——。
这声音如同发自脚下,又像来自远方,风想干什么?风不让旗帜休息。旗的耳边灌满扑拉拉的声响,以为自己早已飘向南极。
风从世界各地请来云彩,云把天空挤的满满当当。风是非物质遗产手艺人,为云彩正衣冠,塑身材,让云如旧日城堡、如羊圈、如棉花地、如床、如海上的浪花、如悬崖、如桑拿室、如白轮船。
风让云的大戏次第上演,边演边混合新的场景。剧情基本莎士比亚化,复仇、背叛和走向悲剧的恋爱在云里实为风里爆发。而风,没忘记在地面铺一条光滑的气流层,让燕子滑翔。风喜欢看到燕子不扇翅膀照样飞翔与转弯,风更喜欢燕子一头冲进农舍房梁的泥巢里。秋毫无犯啊,秋毫无犯。这是风对燕子的赞词。
风吹麦地有另一付心肠。它摩挲麦子金黄的皮毛,像抚摸宠物。麦子是大地养育的奇迹之一,黄金不过之二。大地原本无好恶,无美丑,无奇迹。大地养育毒蛇猛兽,还会分别万物吗?可是麦子不同,麦穗藏的孩子太多,每条麦穗都是一大家子人。
麦粒变成白面之后,世上就有了馒头面条。上天喜看饥饿人吞吐吃馒头面条比皇帝满足。人虽坏,也得活,是五谷而非金融衍生品养育着他们。
植物里,麦子举止端庄,麦穗的纹样被人类提炼到徽章上。风吹麦地,温柔浩荡。风来麦地,又来麦地,像把一盆水泼过去,风的水在麦芒上滚成波浪。风一盆一盆泼过去。麦浪开放、聚拢、一条起伏的道路铺向天边。麦穗以为自己坐在大船上,颠簸航行。
风从鲜卑利亚向南吹拂。春天,风自苔原的冻土带出发,吹绿青草,吹落桃与杏花的花瓣,把淡红色的苹果花吹到雪白的梨花身上,边跑边测量泥土的温度。
风过黄河不需桥梁,它把白墙黑瓦抚摸一遍,吹拂江南蛋黄般的油菜花,继续向南。风听过一百种叽哩呱啦的方言,带走无数植物的气息,找到野兽和飞鸟的藏身地。风扑向南中国海,辨识白天的岛屿和黑夜的星星,最终到达澳大利亚的最南端。
在阿德莱德的百瑟宁山,风在北方的春天见到这里的秋天。世上有二样存在之物无形,它们是时间和风。风说:世间只有速度,并无时间。风一直在对抗着时间。
风吹在富人和穷人的脸上,推着孩子和老人的后背往前走。风打散人的头发,数他们每一根发丝。风吹干人们的泪痕。风想把黑人吹成白人,把穷人吹成富人,把蚂蚁吹成骆驼,把流浪狗吹回它的家。
风一定想吹走什么,白天吹不走,黑天接着吹。风吹人一辈子和他们子孙一辈子仍不停歇。谁也不知风到底吹走了什么,记不起树木,河土和花瓣原来的位置。风吹走云彩和大地上可以吹走的一切,风最后吹走了风。
我至今尚未见过风,却时时感到它的存在。沙尘不是风,水纹不是风,旗帜不是风。风长什么样呢?一把年纪竟没见过风。风与光一样透明、一样不停歇、一样抓不住。
不知不觉,风吹薄了人,吹走了人的一生。
美文 推荐
散文丨王雁翔:我的田野记忆
散文 | 王雁翔:几重春色逐灯来
散文丨王雁翔:那些渐行渐远的生活
散文丨王雁翔:悄无声息的悲伤(上)
散文丨王雁翔:悄无声息的悲伤 (下)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